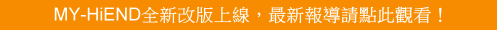
-
2013-06-11, 01:58 PM
#791
 黃鋼---朝聖之路 黃鋼---朝聖之路
黃鋼這幾年因為作品控管問題
價格很低迷
不過經版作品中
還是會不時出現好作品
值得注意

Uploaded with ImageShack.us
-
-
2013-06-11, 02:00 PM
#792
 黃鋼簡介 黃鋼簡介
黃鋼
黃鋼HuangGangb.1961
1984畢業於中央工藝美院
1991獲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碩士學位。並獲得“平山鬱夫”獎學金。
1991任教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
1995獲首届北京國際環境藝術展銀獎
1995接受法國費加洛雜誌採訪
1997參加中國國際藝術博覽會
2000個人作品展,J畫廊,香港
2000個人作品巡展,德國墨尼黑、柏林、漢堡和法蘭克弗
2001個人作品展,法國巴黎
2001參展亞洲藝術博覽會,紐約
2001參展亞洲太平洋藝術博覽會,美國
2001參加“科學與藝術”展,中國美術館,北京
2001個人作品展,來弗士畫廊,瑞士日內瓦
2001參加“Insearchof”畫展,沃時畫廊,美國芝加哥
2002參展紐約藝術博覽會,寶林畫廊
2002參展上海藝術博覽會
2003亞洲現代藝術聯展,沃爾茨畫廊,美國西雅圖
2002作品參展芝加哥藝術博覽會,沃時畫廊,美國芝加哥
2003個人作品展,組閣畫廊,美國聖.達菲
2004中國藝術家聯合巡展,匹茲堡藝術學院畫廊,美國
2004參展北京國際畫廊藝術博覽會,北京
2004參展韓國國際藝術博覽會,韓國漢城
2004參展北京798藝術節
2005參展北京國際畫廊藝術博覽會,北京
2005個人作品展,安娜寧畫廊,香港
2005個人作品展,組閣畫廊,美國聖.達菲
2006參展北京藝術博覽會
2006個人作品展,現代畫廊,台灣
2008中國新潮,現代畫廊,台灣
-
-
2013-06-11, 02:25 PM
#793

淡季不淡旺季來 福貞股價新高
2013/06/11 14:04 中央社
(中央社記者許湘欣台北2013年 6月11日電)馬口鐵包材大廠F-福貞 (8411) Q2淡季不淡,股價今漲停再創掛牌來新高。法人指出,Q3進入全年最旺季,Q4新產能加入,全年營收估逾90億元,大陸市占坐二望一。
Q2原本是福貞的淡季,不過,今年中國內需市場消費力道超乎預期,加上去年同期基期低,福貞繼4月營收創下歷史單月新高後,5月持續維持在滿載高檔水準,達8.78億元,年增高達96.02%,前5月營收已達38.3億元,年增95.57%。
在營收帶動下,福貞近來股價也表現強勁,今天衝上漲停達112.5元,創下掛牌來新高。
展望第3季,福貞副總經理李毓嵐指出,Q3向來是全年最旺季,今年看來消費力道增長,產能可望持續維持滿載。
法人指出,由於馬口鐵可加熱特性,Q4隨著景氣回溫,市場持續看好,福貞Q4產能仍可望維持高檔,全年營收上看96億元,以去年市占第2名的中國中糧去年馬口鐵罐部分營收約新台幣80億元來看,排名第三的福貞今年有機會往前一名。
且Q4起福貞擴產的新產能將陸續加入,後續營運成長力道將加大。
-
-
2013-06-13, 11:18 AM
#794
 8411 8411
精實新聞 2013-06-11 18:53:03 記者 萬惠雯 報導
中國馬口鐵三片蓋包裝大廠F-福貞(8411)表示,第二季中國終端消費市場持續呈現正面樂觀情勢,終端客戶消費市場鋪貨及銷售熱絡,反應有別於往年Q2進入淡季情況,F-福貞主要客戶群與去年同期下單保守相比,拉貨力道積極,產能滿載可直達Q3水準。
F-福貞5月份自結合併營收為8.78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96.02%。
F-福貞表示,F-福貞深耕中國市場已近二十年,目前於中國大陸福建與山東各有一生產基地,今年則規劃籌建新增廣東福貞與湖北福貞兩處製罐基地,擴及兩廣及華中地區,並和福建與山東兩處基地互聯,配合客戶發展腳步逐步增加空罐生產布局,再拉升集團年產量及銷售量,預計集團2013年年產能將躍升至25億支,進一步提升產能實力。
F-福貞表示,公司為少數打入中國本土品牌飲料供應鏈、可直接連結中國內需與民生消費市場之台商企業,主要營業項目為馬口鐵包裝容器之製造與銷售。福貞具備裁剪、塗黃、彩印、製罐及製蓋生產線,提供客戶兼具產能與速度的一站式服務;高達54種罐型的客製化程度,吸引眾多不同類型客戶;擁有技術成熟且經驗豐富的團隊,能配合客戶製作少見規格罐型。
F-福貞表示,公司目前客戶群包含廈門銀鷺集團、承德露露集團、廣州明旺公司、廣藥集團(廣州王老吉大健康產業有限公司)、泰山(漳州)公司、海南椰樹集團、河北養元匯智飲品、福建達利集團等知名飲料食品大廠,外銷則含括美國、加拿大、印度、菲律賓、葉門等地。終端飲料產品在中國大陸內地暢銷,加上中國市場持續穩定成長,使得業績表現亮眼,並於未來有持續穩健發展空間
-
-
2013-06-17, 06:03 PM
#795
 梅忠恕---在閣樓的聚會 梅忠恕---在閣樓的聚會
這是我第一張入手的東南亞藝術家作品
梅忠恕算是越南國寶級畫家
這張在閣樓的聚會算的上是梅忠恕的精品了
ps: 這張是水墨絹本

Uploaded with ImageShack.us
此篇文章於 2013-06-17 06:06 PM 被 wjhuang 編輯。
-
-
2013-06-18, 09:58 AM
#796
 曲磊磊---躺在花毯上的女人體 曲磊磊---躺在花毯上的女人體
第一次看到曲磊磊的作品時有被震撼到
水墨不像油畫可以塗改
水墨作品可以將光影表現得如此精妙實在精彩
可惜只有搶到一張

Uploaded with ImageShack.us
-
-
2013-06-18, 10:05 AM
#797
 曲磊磊簡介 曲磊磊簡介
曲磊磊:1951年生,自幼学习传统中国书画,后自学西方艺术,1982~1985年任北京中央电视台美术设计,1986年进入伦敦中央美术学院,1989年后作为职业画家,在伦敦、巴黎、纽约、威尼斯等地举办多次个人展览,历任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牛津大学拉什金美术学院,英国皇家美术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苏富比拍卖行,佳士得拍卖行等客座中国艺术讲师。1999年起,任英国中国画画家学会主席。2000年获英国政府颁发"教育奖".近年重要个展有:2005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诗"个展,阿什莫利安博物馆,牛津;2007年,"笔墨光影"个展,蕾达。弗莱彻画廊,上海,等。其他职衔:英国中国画画家学会主席,南京书画院特聘画师兼艺术顾问。
曲磊磊我一直站在最原始的出发点上
采访:刘娟娟
采访曲磊磊的过程绝对"省事",你会发现他早已做足一百二十分准备,几乎是自己按着事先收到的提纲自顾自"飞流直下三千尺".他喜欢引用中国古文来表辞达意,这源于他所受过的良好传统教育。他跌宕的人生经历,交织着1950年代人的群体记忆,亦是那一代人的典型个人命运。
回望星星时代,他表达得最多的便是,"我们评论艺术品的本身已经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现象已经发生了,把当时艺术被引导到的极端形式的链条打破了,换句话说,就是当年星星点了一个火,到85的时候开始燎原……"如今成功跨越中西方艺术文化的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经过反反复复的坎坷,和艺术实践,才找到了人性价值,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在中国的三十年的时间写了一个"撇",在西方的二十来年中写了一个"捺".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
《生活》:你目前的艺术工作有哪些?
曲磊磊:现在国内外一些人筹备做2009年"星星三十年回顾展",我跟黄锐他们商量了,计划做一个国际巡回展。我们希望展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年那些画,不管怎么划定,1979到1980,或1978到1984都可以算星星时期。第二部分是星星画会主要成员从1979年到2009年这三十年中的画。现在的策展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和追捧比较片面,都有意无意地把"星星"放一边了,主要宣传"85新潮"和"后89".整个西方艺术界和艺术市场,比较知道85以后,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开端并不了解,所以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认真探讨这段历史,也给星星应有的地位,这个意义特别大。
《生活》:在79年之前,你个人的绘画积累怎样?后来怎么认识其他成员?
曲磊磊:我从小就学传统中国画,虽然我这一代人主要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长大,但走运的是,我在家庭学校也受到了相当的传统文化教育,古诗词、古文学、哲学、医学,书法……后来我发现中国画不足以表现生活中的感受,就一门心思地学西画,从欧洲古典主义一直到现代的抽象主义,通通都走了一遍,还认认真真到医科大学去学了人体解剖。我也曾经学过写诗,但后来发现我不会成为特别好的诗人,我就放弃了。
1977年左右,文革结束,我和几个朋友就酝酿着出刊物,商量得有点眉目的时候,听说有本书已经出来了。古文里不是说"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真正你想到的,正是千万人都在想的事,这本刊物叫《今天》,我们就到了《今天》编辑部,当时北岛、芒克、黄锐、江河、多多、顾城……后来在诗歌界比较有名的人,基本都是在这个圈子里。我给《今天》画了一些插图,每一期都贴在西单民主墙上,有时晚上就被人揭走了,然后再画再贴,甚至一张画画六七次,特别受欢迎。
当时黄锐任《今天》的美术总监,他和马德升、阿城已经在准备画展,后来加上我,我又推荐了王克平,以后逐渐又有薄云、严力、李爽,艾未未、毛栗子等。由于每次跟美协申请办展览都是令人失望的结果,大家决定就9月27号,在美术馆后面,画展的名字想了好多主意,后来王克平说,叫星星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哎!不错!就定下来了。然后开始分工,筹钱买框子,租三轮车,做海报什么的。27号早晨画都被挂出来了,就整个很轰动。
两次星星美展的布展都是从我的画开始的,而且第一张画就是一个裸体飞在天上,黑白的画,表现生命对自由的追求,我现在还有当年的一些报纸,国外的报道,北京发生这么一个事,外国记者就都来了,就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展,因为画展很快被封了,很快又发展为游行了,变成了一个事件,后来的报道就更多是针对这个事件了。
《生活》:"星星"出现的偶然性或必然性是什么?
曲磊磊:实际上现代艺术,从徐悲鸿和刘海粟这代人已经致力于做了,由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等各种原因,这个路走得是相当艰难,后来赶上革命和战争,中国的现代艺术整个走上了歧途,变成了宣传的一部分,解释政策的东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跟生产劳动相结合,特别是到文化革命中,把艺术推向了非常极端的教条主义和宣传方针的路子上去――就是我们一直在批判的西方的形式主义,其实我们是做了一种真正的形式主义,真正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就把艺术走得非常偏了。当然就跟真正的"人"本身、人的生活、生存、生命状态,相去甚远。
所以我们当时是不约而同的、自发的,在偶然的命运驱使下走到一块儿。见面以后,发现你和我的东西,虽然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完全不一致,但内在的东西,对艺术的诉求和理解,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是一致的。我觉得这倒对了,就像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我们所谓挑战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小人同而不和",大家搞的东西全都一样,但互相斗得死去活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星星是在那个时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现象,它也是一种必然。
文革后到80年这段时间,把它叫理想主义的一代,叫觉醒的一代,叫思索的一代,叫伤痕……不管怎么叫吧,这一段时间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文学上有比较著名的伤痕文学,有以《今天》为代表的朦胧诗和现代文学运动,摄影方面有"四月影会",有人开始做现代音乐,美术界有上海的十二人画展,北京的无名画会,星星画会,油画研究会,同代人,等等,整个是很大的动荡思潮。
所有的经历都在引导你
《生活》:今天客观地看星星时代,它的粗糙和致命伤在哪里?
曲磊磊:当年的作品从艺术表现、艺术修养上,是比较幼稚,因为我们可以接触的国外信息非常少,是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本身对艺术的理解。但不能否认,那种生动的、新鲜强大的生命力、对不公正的挑战,对自由的追求,对自我意识的诉求,都是中国人久违了的一些东西。当时全北京的人恨不得都来看展览。这些画跟当时的诗歌、文学结合起来,也有它很多的文学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在里面,所以在当时引起这么大的轰动。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讨论当年星星在艺术上的东西,其实意义并不太大,意义最大的是这个事件发生了,我们做了这件事,把艺术被引导到极端形式的链条打破了。换句话说,就是当年星星点了一个火,到85的时候开始燎原,当时叫星星也有这个意思。
《生活》:回忆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你触动最大的具体事件或人物还有哪些?
曲磊磊:就我个人来讲,思想上的转变是从71年开始的,就是林彪事件。我参军就是林彪的部队,我父亲也属于林彪的系统,林彪在我们心目中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居然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我才重新对所有的问题开始反思。那一年中国的经济也非常危难,开始跟美国改善关系,尼克松访华等,从那时看问题都有更深一层看法了,更深一层研究中国的问题,看很多很多书。之前的文革我也都经历了,上山下乡,后来当兵、当工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我触动最大的事,基本都发生在1976年,1976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可以把中国上下五千年方面面面的历史、文化、心理结构都融括进来,而且这是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太重要了。从周恩来去世,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天上降流星雨,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之后各派势力的焦灼状态,然后毛泽东去世,中国预言都说,天崩地裂要改朝换代,就在全国可能将有大乱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戏剧性的命运转折,把四人帮给抓起来,文化革命结束。这一年发生的事情真是太不得了了。恰恰在这一年,我因为电视台的工作,去了西藏、去了各种地方,接触了很多人,去了唐山大地震救灾现场,住在帐篷里,我第一批完全表现内心的画就像泉水一样,从笔尖流到笔记本上,这是我艺术生涯上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起点,我学这么多年画,始终想有一种方式像说话一样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在那种状态下一下子出来,后来星星美展我展的好多都是那时期的画。
《生活》:你在国内的三十年,有着很丰富的人生经历……
曲磊磊: 现在有个英国作家在写我的传记,想探讨我大半生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跟她说,就是寻找人性之路,怎么把迷失了的人性通过一种反反复复、坎坷痛苦的经历找回来,再把它发扬,这是我整个生活和艺术的主线。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从小就是被有意识地塑造成某种类型的人,用西方的话说,就是干干净净被洗脑了,从小生在毛主席身边、世界革命的中心,是最幸福的一代人,今生所有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去解放全人类,毛主席一声号令,我们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到上学时候提倡雷锋和王杰,整个个人的生命完全没有价值,最重要的是体现整体的价值、观念的价值,你是一个齿轮和螺丝钉,在革命的机器上,一辈子在那儿闪闪发光,这是我们年轻时候所接受的。当时为了一种正义和真理去献身是非常崇高的行为,这从现代文明的观念来看,是非常之可怕的。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一群兵马俑,气势宏大,浩浩荡荡,完全没有个性,活着为他战斗,死了跟他殉葬。这种东西我是经过长时间的磨难,经过运动中的那些痛苦回忆,各种各样的事,才慢慢悟出来的。
做知青到乡下去,现在有很多人回忆知青生活,我觉得我跟他们的感受都不一样,我上山下乡时是非常兴致勃勃,带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生活艰苦之极,那段回忆是特别宝贵的,当然也有很多疑问,很多苦恼。后来参军,正在我欣欣向荣的时候又一个打击,从北京公安局转来一份材料,说我在学校时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在军队发展的路就堵死了。之后回到北京从头开始,当工人。这些阶段都一直在画画了。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挫折也好顺利也好,你走的每一步都是非常宝贵的,所有这一切经历都把你引导到某一方向上去,有一条潜在的线在引导着你,重要的时候你自己能够看到这条线,而且能把握这个方向,那么生活就比较有意义,怕的就是自己看不到这个,而且迷失了,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这是最可怕的。
"桔生于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
《生活》:大多数星星成员后来在艺术成就上都不大,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曲磊磊:我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同的看法,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成就很大,这就不客气地说了。就说成就的判断标准,以艺术界学术界的认可是一种,商业的认可、画的卖价是一种,对艺术品艺术价值本身的判断又是另一种标准,判断艺术成就不是太简单的事。
从79年以后,这三十年来,我有很大的成就。第一点,我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在中国的三十年的时间写了一个"撇",在西方的二十来年中写了一个"捺",我认识了我自己,找到了人性的价值,这是经过反反复复的坎坷,和艺术实践,才得到的东西,是非常重大的成就。
第二点,是人性的复归,我们迷失了的人性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我们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状态,生命的价值在哪儿,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性的尊严是什么。我这三十年来一直在坚持最开始到星星的初衷,站在最原始的出发点上,从这个出发点往前走。这个出发点也是星星画会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价值和精神遗产――回到艺术的本源。
第三点,在自我表现的形式中,艺术其实还是生命对自由和价值的追求。目前在英国的博物馆、大学、民间团体,任何一个机构如果谈中国艺术,不谈我的名字是不可能的。从学术上来讲,05年时,牛津的阿什莫利安博物馆给我做一个个展,专题是"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诗",英国的主要博物馆给在世的中国画家做个展,这个展览是第三个,第一个是上海画家朱屺瞻的百岁展,第二个是吴冠中的回顾展。这也是阿什莫利安博物馆1726年建馆以来第一次给在世画家做个展,据他们说是迄今为止办的最成功的展览之一,这就是学术上的最高肯定。从商业上来讲,我的画现在还没有像这些年炒"85新潮""后89"那种没有道理的天价,但是同代的画家应该算是不错的。现在威尼斯双年展、北京双年展也都邀请我,所以不能说没有成就。
《生活》:初到英国,生活是什么情况?怎么进入英国艺术界?
曲磊磊:我出国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国内当时很被动,二是我也想去看看世界。被动呢,星星美展还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是我惹了一个大事,当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照明,审判魏京生的时候我录了音,后来单位重要的工作都没我的事了,我就打算辞职,另外, 1980年我还参加了一次中央美院的研究生考试,总分第四,但那年收七个研究生,就没有我。我妹妹当时在英国,就说要不让我先出国看看,我说也好,结果一看就看了这么长时间。
刚英国我什么都干的,因为我吃过苦。但当时我有个信念:老鹰有时可能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老鹰那么高,我可以什么都做,但是我不是只能做这些事。出来时候带了一卷画,有个美联社的记者朋友很喜欢,帮我办了一个展览,卖了几张,更重要在展览时认识了比较上层的一批人。一件事总能引导到另一件事,局面就逐步打开了。我也会在街上给人画像啊,我想也总能认识几个人吧,在饭馆洗盘子啊、烫衣服啊,也想办法学点资本主义的东西,买股票什么的,什么事都做过。
我后来发现英国有人特别热衷中国文化,愿意学中国传统画,这促使我又把中国传统的东西给捡起来了,中国有"为人师表,不能误人子弟"的职业道德,我又把中国的美术史从头理了一遍,几大领域、流派的各个代表人物,他们的主张、技法、特点,通通研究一遍。我在国内是一门心思地研究西方的东西,反而是到了国外以后又回过头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这种双向的逆反心理其实是非常有力的,有一个距离,就看得更清楚。我认真地教嘛,人家也认真地学,后来就越弄越大,越弄越好,英国现在有一个中国画家学会,一千多会员,我是名誉主席,我的学生画的东西,很多你看不出来是外国人画的。现在这个学会走到哪儿到处都有我的学生,有点桃李满天下的感觉。2000年政府给了我一个教育奖,千禧年得这个奖,是唯一的外国人传播外国文化的,所以这样就在学术上有了地位。其实最开始是为了赚钱吃饭,后来就做成传播中国文化了,这样说的话就责任重大了,不能误导,真得把传统给人讲清楚,谈到历史、哲学,谈到那些非常深奥的东西,就一步一步做起来了。
在这同时,我照样做我的现代艺术,在经济上、语言上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了。到一个地方要进入它主流社会,我的接触范围也很广,从首相到银行家,一直到街上的乞丐,通通都有朋友,艺术家的地位就特别容易交朋友,就逐渐就扩展了局面,进入这种文化了。
《生活》:中西方两种文化的跨越,如何影响你在艺术上的转变?
曲磊磊:不同文化之间的结合,有很多是成功的,也有很多是失败的,这就涉及到你到底处在什么位置上,到底要什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英文说"neither this nor that",有些不成功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夹在两种文化之间,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在英国进入不了主流社会,对英国文化了解不深,远离中国,又对中国文化知之甚浅,两边够不着。另一种情况是"either this or that",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我认识很多人,就干脆切断跟中国的联系,中国话也很少说,他可以生活得很自在,完全进入这个社会;有一些呢不行,在这儿怎么也融不了,最后就回到中国了,这种也好,他至少能够上一头。我所追求的状态是"both this and that",既是这个也是那个,能够驾驭两种文化,不是被挤在中间。现在我回到中国有一种归属感,根在这儿,朋友也很多,非常愉快,回到英国同样也有归属感,我的家也在这儿,我也进入这个社会,所以这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艺术跟生活同样的道理,有些人现在就是跟中国传统一点关系没有,完全跟着西方的潮流走,也走得很成功;还有些完全排斥西方的,国粹派的一大批人,按照中国传统路子;也有的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干脆就大拼盘,这个弄点那个弄点,像把大字报和可口可乐一凑,我觉得很肤浅,当然他也可以在商业上很成功。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是我们大家不断在讨论的问题,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讲,这不是问题,你把你心里的东西真正地弄清楚,真诚地,用你全部的本事、最好的办法表现出来就可以了,最后出来的东西肯定既是这个也是那个。因为作为人,我们肯定是生活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之间,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你自己的笔墨属于你自己的,把你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那一定是属于时代的。
比如说我画了一批水墨的英国风光,卖得很好,查尔斯王子也收藏,英国的云天、教堂啊,非常漂亮,很适合用水墨画,但视觉上全然不是原来的中国山水画,"桔生于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不同了,你看到的东西,表现的东西也都不同了。还画了一批英国人生活的,平常看到的酒吧间、花园、乞丐、大老板……都是水墨画,我题上诗,特别受欢迎。这是一种桥梁,他们本来对中国水墨画很不容易理解,但是画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很熟悉,然后提上诗,英国人又讲究那种幽默感,一下子他们就都懂了,这也是我尝试的一部分。
1989年,我突然变得清醒了,在国内三十年的生活、文化、民族、历史都觉得很清楚了,意识到了我应该做个什么画家,就回到了原来搞星星的出发点,当初是自发的、朦胧的追求,到89年就成熟了。我做了一系列直接相关生活主题的画,我把它叫做《梦中的太阳》,或是《我的半生》,都完全没有商业和展览目的,纯粹为自己做,就特别开心,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把绘画、书法、题辞、拼贴……我所有的本领全都用上。但后来佳士得拿去拍卖,比我平常卖的画高十倍都不止。
到了95年左右,我就想做寻找人类共性的东西,即将结束的一个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迅速的世纪,同时也是最血腥、最悲哀的世纪,跨越种族、文化、信仰,人的情绪其实是一致的。我不喜欢小里小气、歪风邪气的东西,我喜欢追求正气,画了一系列画,所有的感觉都通过不同的手的形象去表达,形式感基本跟《我的半生》差不多,但是又往前走了一点,表现情绪的主题绘画都比较大,还是用水墨,但造型都是西方的,雕塑式的光影手法,主题我叫做《此时此地,面对新世纪》,99年威尼斯双年展展了,英国一个画廊也展了。
新世纪开始后,我的创作又从共性回到个性,倾心地投向生活中的普通人,有教师,农民,外交家,诗人,家庭主妇,失业者,乞丐,战争的幸存者,等等,主题叫《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诗》,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探讨,去揭示人性的普世价值,这个主题展出后,在英国学术界和大众中都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可。
最近我又开始走新的一步,想作美学上的,唯美主义的探讨,叫做《笔墨光影》,我画了一批人体,同样还是水墨、宣纸,造型方法是西方古典主义的。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水墨如果解决光和影的问题,光和影在中国艺术史上完全是一个禁区,阴影好像是比较贬意的东西,但光影在西方艺术上恰恰是最核心的东西。同时其他的项目也在继续,人的生命价值的东西也还在继续在画。说到底,不管我画什么,画的还是我自己,我对人性、生命的尊重和理解。
《生活》:现在和当年的星星成员再相聚,觉得大家有何改变?
曲磊磊:我们现在都是老朋友,当时等于是共过患难,后来大家走的路子都不一样了,有的去弄房地产,做什么的都有,艺术家们的路子也都不一样了。就是说,星星画会作为一个实体已经不存在了,星星该做的基本做完了,所要起的作用那时也已经完成了。星星十年展在香港时,外界褒贬不一,我们当时很冷静,咱们该做的事早就做完了,现在聚在一块,还记得这个事,还有回顾,有感情,但今后全靠大家自己。二十年展在东京时,情况就好一些了,大家都有一些新作。现在三十年展,我更希望能看到这三十年的发展,每个人星星之后的路怎么走的,你现在走到哪儿了。如果你现在今后做得好,星星无疑是光荣历史,如果不好,那星星仅仅是一段历史而已,因为当代艺术已经走得很远了。 当然,对于任何一段时间的历史,它要有一段时间的筛选,所以现在谈什么好什么坏,还为时过早,对于画家自己,还是怎么把东西做好,而且在现在这种物欲横流的商品大潮下,怎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明确的方向,能够安于寂寞,甘于清贫,乐于默默的,长时间的画室工作,把一件艺术品做好,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
-
2013-06-18, 01:25 PM
#798
 蘇笑柏---一意 蘇笑柏---一意
Uploaded with ImageShack.us
此篇文章於 2013-06-19 03:29 PM 被 wjhuang 編輯。
-
-
2013-06-19, 03:32 PM
#799
 版畫 版畫
最近市場上趙無極與朱德群的版畫非常熱門
版畫對一般剛接觸藝術的人也是非常好的入門選擇
尤其是名家版畫
以趙無極 朱德群 版畫來說
這十年來增值幅度也大約有30倍的報酬率
可以說是極佳的投資與居家裝潢的標的物
最近也收了一些版畫
後面再來跟大家分享
-
-
2013-06-19, 07:16 PM
#800
-
 發文規則
發文規則
- 您不可以發表新主題
- 您不可以發表回覆
- 您不可以上傳附件
- 您不可以編輯自己的文章
-
討論區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