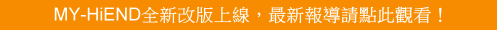
-

 作者: wjhuang

張洹用香灰做畫
這個屌吧!!!

談香灰畫
新京報:2005年回國為何想到定居上海,而不是回到北京?
張洹:你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想走了。我在紐約待到第三年時,所有的活動都去參加,就對那個城市失去神秘感。正好當時中國在上升,國力、經濟、文化都在上升。回到國內這種刺激就很強,就回來了。但北京我已經很熟了,有一堆朋友,太了解了。在上海待這麼久之後我可能又要換一個新環境。
新京報:回國後怎麼想到創作起香灰畫?
張洹:這與我離開國內8年,突然回到國內的寺院有關。那種感覺很親切,讓我重新認識了寺廟。當時我是在上海的靜安寺對香灰這種材料有了重新發現。我看到那麼多男男女女在那自言自語,就在想究竟他們被給予了什麼力量,讓他們敬香拜佛。我覺得香灰這個材料具有靈魂性。它與油畫、水墨不同,香灰融入了許多人的願望、祝福。在那瞬間我感受到香灰的魅力和魔力。我想香灰這個材料應該屬於我,應該屬於藝術史。我拿到這個材料,三天三夜睡不著,心情非常複雜。
新京報:現在國內提起張洹,就説是創作香灰畫的。
張洹:香灰是一個新的門類。我不會壟斷,但我們也有專利。如果你自己畫香灰畫就犯法,如果得到我們工作室批准就算合法。
新京報:我們從來沒聽説畫水墨畫、油畫要向某個地方申請才能創作吧?
張洹:香灰畫裏面除了香灰之外,還有藝術製作過程。我們未來會寫書説明怎麼製作香灰畫這一藝術作品,這是我們這個團隊研究出來的。
談當代藝術
國家變化帶動藝術創作
新京報:2005年你回國後正好經歷了中國當代藝術非理性的高速瘋狂發展階段,你自己有感受嗎?
張洹:那是國家在變化。全球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個時期這麼特別。經濟沒有經過像歐美國家那樣的長時間積累,都是新錢。而藝術這塊也呈現出亂、膨脹的局面。不過亂也好、膨脹也好,這是好事。不管怎麼樣,成功也好,商業也好,先亂起來,慢慢地就會看到最後誰能留下來。因為總是要經歷這個階段,每個國家都必然要經歷這一段。
新京報:你平常關注自己作品的拍賣價嗎?
張洹:我從來不看拍賣市場,也不關注我的作品的拍賣價。我只知道,我去每個城市都有我很多藏家,每個藏家都會過來對我説:我有你哪個時期的作品。
新京報:那你聽説過當代藝術F4的稱號嗎?當年方力鈞、岳敏君他們正是因為拍賣價格一起進入百萬美元俱樂部而被封號。
張洹:我聽説過當代藝術F4。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分類啊、排排名次,挺好玩的。當然,我不在這個名列中。我挺為他們高興。中國藝術家能與西方藝術史上的大師作品價格拉近,應該是好事。從藝術本身來講,我們應該比他們還貴。今天應該遠遠超過他們。
談工作室
讓工作室變成一種新的模式
新京報:你在上海佔地50畝的工作室被稱是一個由百餘人組成,是全球最大的當代藝術工作室。
張洹:我原來還可以叫出工作室成員的名字,但現在已經叫不出了。現在比那時正規多了。我們要把它徹底正規化、公司化。我想5年內至少(達到)500人。
新京報:是創作香灰畫這一領域讓你工作室有資本不斷擴張嗎?
張洹:跟這段時期沒什麼關係。我在美國8年積累的錢,已經能讓我可以有工作室,可以有飯吃。2005年時,我可以10年甚至20年不賣一件作品,來養我的工作團隊。
新京報:之前大家對藝術家的創作更多的認識是個體的創作行為,但是我們看到新世紀10年誕生了各種工作室。藝術家請助手幫助創作被認為形成了一種藝術生産線。你是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張洹:我想把這個工作室做到極端化,讓它影響很多人。我想讓工作室變成一種新的模式。但這種新模式一點都不流水線,我們的作品都是一版一個,不是可以不斷重復的,不像做皮鞋那樣。
談西方視角
他們不尊重我們的藝術
新京報:國外對你的作品很欣賞吧。
張洹:1998年全球對中國當代藝術已經展了一遍了。我出國時已經做好準備打工,結果就有人收藏我作品了。後來《紐約時報》做我的頭版報道,我就有了在紐約一畫廊做個展的機會,並被紐約一個很大的收藏家全部買斷。這很傳奇。
新京報:2006年,美國著名當代藝術史學家喬納森費恩伯格的當代藝術史著作《1940年以來的藝術———藝術生存的策略》第二版出了中文版,將你和蔡國強、馬六明等數位中國當代藝術家都納入書中。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你在學術上被認可。
張洹:我45歲了,都快50歲了,進入歷史也正常。人生那麼短暫,我只在乎生活要幸福、健康,要活得正常。
新京報:據説大家把你跟達明赫斯特比。但你好像不太高興。
張洹:全球對我的評價都很高。我也不是比他們強,是不一樣吧。西方人都不懂藝術,他們都説GREAT,都説好,他們不尊重我們的藝術。他們站在外部的世界來看中國藝術,完全放在政治背景下
-
 發文規則
發文規則
- 您不可以發表新主題
- 您不可以發表回覆
- 您不可以上傳附件
- 您不可以編輯自己的文章
-
討論區規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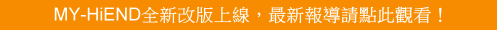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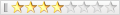




 回覆時引用此篇文章
回覆時引用此篇文章